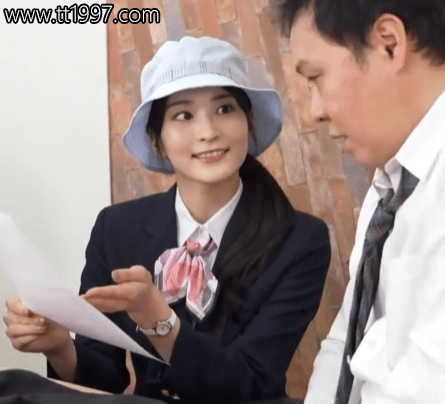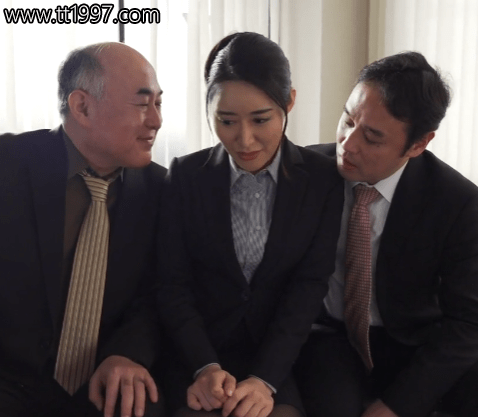本城花(Hana Honzyou,本城はな)今年三十七岁,住在长野山脚下的一个旧木屋里。她每天的生活几乎可以用“重复”来形容:早上五点半起床,喂猫,做早餐,去山边捡一些枯枝或松果,然后泡上一壶很淡的红茶,坐在窗边开始一天的手工活。但她的作品,从不重复。她在网络上卖自己制作的木雕、陶器、小挂件,所有的作品都只做一件,从来不复制。每一个买家都知道,自己买到的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版本。

电影番号HMN-718就像在观察她的生活,但比起流水账似的记录,这部片子更像是一封被慢慢展开的信,一封本城花写给所有“坚持做自己”的人的信。镜头从来不快,它总是慢悠悠地晃过她削木头的手,泥土在她指缝间流动的样子,或者她在电炉前烘干陶杯时盯着火焰出神的眼神。导演显然不急,他让我们一点点地进入这个女人的世界。本城花不多话,她也不需要多说。她的每一个动作,每一件成品,都是她在说话。
故事的开端是一封奇怪的电子邮件。标题只有五个字:“我想找你”。内容只有一句话:“我想要一件不会碎的陶器,可以吗?”没有署名,没有地址。一般人可能就当成骚扰邮件删掉了,可本城花没有,她反而认真地回了封信。她问:“为什么你需要它不碎?”过了整整十天,对方回了一封长信,说自己母亲刚去世,留下一个老旧的茶杯,每次用都担心会不小心打碎,想要一个“替身”,一个不怕岁月、不会因为失误就失去的器皿。

于是,本城花花了三个月时间,去找一种特别的复合土,用松脂和碎陶粉混合,在海边的旧砖窑里烧了六次才烧成功。那个杯子,通体灰蓝色,像是傍晚还没完全暗下来的天空。寄出去之后,她收到了对方的第二封信:“谢谢你,我终于敢喝茶了。”
从这之后,她的订单越来越多,但每一个都不是“我要一个杯子”这么简单。每一个都像是一个谜语,需要她花时间去解答。有人写信说:“我希望你能做一件能让我不再梦到他的小挂饰。”她做了一个白色陶猫,猫眼睛闭着,嘴角带笑,尾巴像是在轻轻扫动梦境;有人说:“我女儿六岁了,她说她最想要一个‘会听她讲话’的布偶。”本城花做了一个布熊,里面藏了一个录音机,录下女孩的声音,每当按下熊肚子,它就会重复那句:“我也爱你。”
影片的主线看似是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订单,但真正牵引着观众的,是本城花自己逐渐变化的情绪线。一开始,她几乎不和任何人联系,除了她那只年迈的橘猫“田七”。但随着一个又一个订单,她开始写更长的回信,有时甚至会主动问候对方的近况。她开始在信里画小图,在包裹上写诗,甚至开始把某些失败的作品“偷偷”寄给看起来特别孤独的客户,说是“附赠的小惊喜”。影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她在变得外向,只是让我们一点点看到她和世界的缝隙变得没那么紧闭了。
整部电影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段落,发生在冬天最冷的一天。本城花收到一个特殊订单:一个盲人女孩希望她做一个“可以听见雪声”的风铃。本城花苦恼了很久,因为雪没有声音,至少不像雨点敲窗那样明确。她最终做了一个风铃,铃体是空心木雕,里面填了细小的银珠子,挂在外头的时候,只在雪堆轻轻覆盖它时发出极轻极轻的声响,像是谁在远方轻轻说了一个“嗯”。女孩收到后回信说:“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,但我真的听见雪在讲故事。”
番号HMN-718这部片并不是没有冲突或高潮,它的高潮很特别,不在于某件事“终于成功”或某个角色“终于面对过去”,而是一种“突然明白”。本城花收到一封她迟迟没回的邮件。寄信人说,他是她的弟弟,在她离家出走的十七年里,母亲一直在找她,直到两年前去世。他附上母亲的照片,还有一张儿时她用彩笔画的纸风车。本城花看了很久没有哭,也没有说话。第二天,她给自己下了一个订单:做一个“能让时间倒流”的东西。
她做了一个旋转木盒,打开时里面有一张照片,一个录音,一小块折叠布,还有一个装着干花的玻璃瓶。她说:“这是我从未寄出的回信。”她自己给自己寄出了那个盒子,然后把回信贴在门口,说是“特别订单,不对外公开”。影片到这里已经快结束了,但观众明白,这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个开始。本城花终于给了自己那个她一直回避的订单。
影片最后,她正在包一件作品,看起来像是一只很奇怪的动物,小小的,有点像猫,又像狐狸。她包得很仔细,然后放在阳光下晒了会儿,再贴上标签。画面一转,是一个陌生人走进家门,说:“你好,我是来帮忙的。”本城花抬起头,对他笑了一下,说:“那你可得小心,我这儿的订单都挺麻烦的。”然后电影就在她那句玩笑和阳光洒落的房间里结束了。
番号HMN-718是一部看似平淡但情绪浓烈的电影。它用一个手工艺人的生活轨迹,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织得细腻又真实。它不像那些高潮起伏的剧情片那样刺激,但你看完之后,会忍不住想给谁写一封信,或者自己动手做点什么送人。本城花不是一个英雄,但她是那种慢慢改变世界的人,她用一点点泥土、一点点布料、一点点木屑,慢慢缝合了许多破碎又珍贵的心。而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吗?安静、独立,却又和世界保持一份真诚的连接。电影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做,但它让你看见,做自己,其实是可以的。
当然可以。接下去的段落,就像本城花的生活本身——无声无息,却藏着流动的温度。
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,本城花原本并不是做手工艺出身的。电影中没有直接交代她的过去,但有一段静默的镜头颇有深意。她在夜里清洗工具的时候,镜头对准她的手指,那些细节之中透露出熟悉键盘的痕迹,而不是工匠的老茧。她曾是城市里的一名设计师,甚至还小有名气。但有一天,她突然消失了,像是从城市的地图上蒸发掉了一样,没人再提起她。这个设定没有明说,而是藏在一组组像拼图一样的片段中,你得自己去拼凑。
有一幕特别动人。本城花收到一个新客户的留言,说自己从小不信任别人,觉得“人说出的话都是包装过的”,问她的作品会不会也是如此“包装”,只是用来博眼球的“个性化噱头”。本城花没回信,而是寄出一块陶片,上面写了一行字:“那你把它打碎试试,看它里面有没有糖。”客户最终没有打碎那块陶片,但拍下它放在窗边的照片,说:“它硬得像石头,却让我觉得柔软。”本城花在镜头前轻轻笑了下,继续雕她的新作品。这种不言说的回应,是番号HMN-718这部电影最令人动容的魅力之一。它不急着讲清楚,而是让情感自然发酵。
有人说她是在帮别人疗伤,但更细心的观众会发现,她其实是在用别人的故事疗自己的伤。每一件作品,都像是她替自己做的一个“练习”:练习接受,练习原谅,练习温柔地放下。就像她曾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做这些东西,并不是因为我擅长,而是我害怕忘了怎么去爱。”这句台词其实只出现了一次,却足够让人在电影结束后久久回味。
电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,因为本城花的故事,其实没有真正“结束”的那一刻。她仍然住在那座木屋里,仍然每天早起喂猫、泡茶、雕刻,只是她的作品多了一些颜色,信件多了一些笑声,包裹也常常附带着一小段诗或者几枚她自己捡来的松果。导演让电影在最平静的时候停下,不是为了制造悬念,而是为了告诉观众:生活真正的高潮,从来都不靠戏剧性的转折,而是那一点点日常中被认真对待的细节。
你会发现,番号HMN-718不像一部“看完就完了”的电影,它更像一个被打开的信箱。你可能不会一口气看完,但只要你走过某个深夜,或经历某个脆弱的时刻,你就会想起她——那个不说大道理、也不炫技,只是静静地,用双手做出一个又一个温柔回应的本城花(Hana Honzyou,本城はな)。她不是救世主,但她是一种答案,一种关于“如果你愿意好好听世界说话,世界也会回应你”的答案。我们每个人,或许都可以成为她那样的人。只需要慢一点,真一点,就够了。